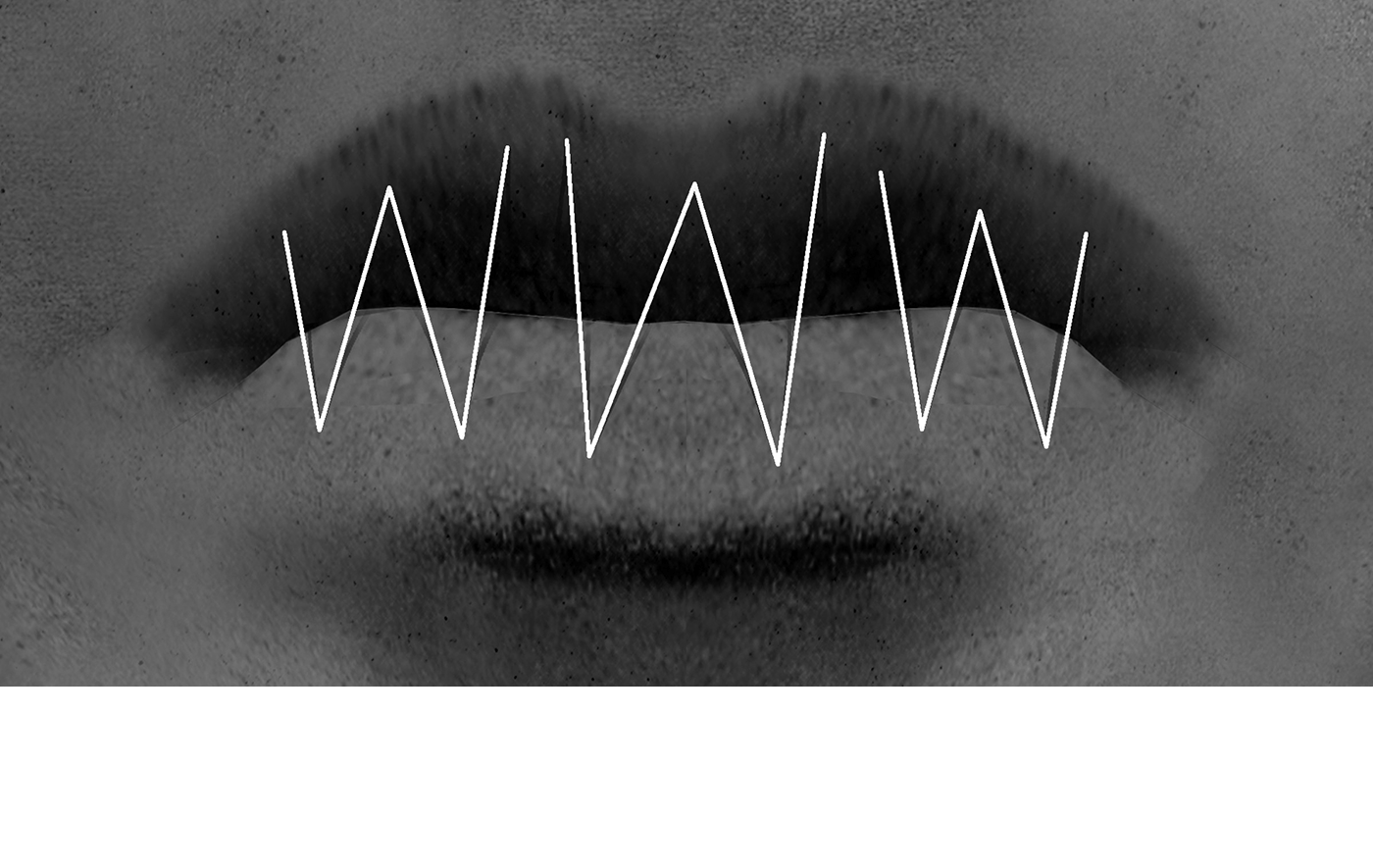人权旨在保护人民免于政府的侵害与漠视。权利对政府的行动划定界限,对政府的作为课以义务。然而,现今新一代的民粹主义者正试图推翻这个保护机制。他们自居为“人民”的代言人,将人权视为他们所谓大多数人意志的绊脚石,妨碍国家抵御他们所谓的安全威胁与邪恶势力。他们不相信人人应享同等权利,主张优先保障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鼓吹一种危险的思想,即在自称代表全民的政府统治下,人民将不再需要为自己主张权利。
民粹主义随著公众对现状日益不满而风行。在西方,许多人因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和不平等加剧而感到失落;骇人的恐攻事件引发民众忧虑和恐惧;还有些人对族群、宗教和种族日益多元的社会感到不安。愈来愈多人认为这些大众关切的问题得不到政府和菁英阶层的重视。
随著不满情绪逐渐沸腾,某些政客乘势崛起甚至攫获大权,他们说人权只是在保护恐怖分子或寻求庇护者,不顾多数民众的生命安全、经济福祉与文化偏好。他们以难民、移民和少数群体为替罪羊,真相往往遭到抹杀,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种族歧视和伊斯兰恐惧症则不断滋长。
这种危险趋势可能吞噬当代人权运动的成就。早期人权运动主要关注二次大战的人性浩劫以及伴随冷战而来的压迫。由于亲眼见证政府可能犯下的邪恶暴行,各国陆续通过各种人权条约,冀求限制及遏止未来的人权侵犯。人权保障被认为是让人们活得有尊严的必要条件。随著人权日益获得尊重,也为更自由、更安全、更繁荣的社会奠下基础。
然而,时至今日,愈来愈多人感到人权不是在保护他们免于政府侵害,而是在削弱政府保护他们的能力。在美国和欧洲,人们心目中的首要威胁是移民,其中夹纒对于文化认同、经济机会和恐怖主义的忧虑。由于民粹主义者的鼓动,愈来愈多民众认为人权只是在保护“他者”而非我群,因此没有存在必要。民粹主义者主张,只要大多数人同意,应可任意限制难民、移民或少数群体的权利。来自国际条约和制度的阻力,在本土主义常较全球主义更受欢迎的今日世界,只能造成人权更加受人厌恶。
或许人性原本如此,认同异己比较困难,剥夺他人权利则更易于接受。人们安于相信一种有害的想法,即他们可以选择性地实践权利──剥夺别人的权利,但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人权本质上不容厚此薄彼。或许你对邻居心有不满,但今天你不维护他们的权利,明天你自己的权利也将不保,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人权的根本。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名义侵犯某些人的权利,就是在挖整个人权体系的墙脚,而所谓大多数人的成员总有一天也会需要人权体系的保护。
若不警惕过去一年出现的野心政客──自诩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实则视人民如草芥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流──我们将自食恶果。当民粹主义者将人权视为实现大多数人意志的绊脚石,他们迟早将把矛头对准异己。当民粹主义者攻击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这种风险将更加提高,因为司法独立旨在维护法治,亦即落实人权对政府行为的制约。
不受约束的多数决主义兴起,以及政府分权制衡机制遭受攻击,或许是当前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危机。
威胁蔓延,应对冷淡
太多西方政治领袖,不去对抗民粹主义兴起,反而流露对人权价值缺乏信心,只愿给予冷淡支持。愿意挺身而出的领导人少之又少,只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美国总统欧巴马偶一为之。
有些领导人似乎学鸵鸟把头埋进沙土,期待民粹主义的风暴早日平息。其他人,若非企图利用民粹主义激情捞取利益,就是设法跟进民粹主义者的政见模糊彼此差异以抵消对手优势。英国首相梅(Theresa May)指责质疑英军在伊拉克实施酷刑的人士为“社运左翼人权律师”。法国总统欧兰德(François Hollande)挪用右翼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策略,企图将其反恐政策重点摆在剥夺法国出生双重国籍人士的国籍,不过后来反悔而放弃这项主张。荷兰政府支持对穆斯林妇女穿戴面纱加以限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呼吁关闭欧盟边界,近来获得许多欧盟国家领袖的支持,使难民陷于险境。这样向民粹主义者东施效颦的做法,只会合理化某些政客对人权价值的攻击。
类似的潮流不只出现在西方。事实上,西方民粹主义者的兴起,似乎鼓舞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更加理直气壮蔑视人权。例如,克里姆林宫积极为总统普亭(Vladimir Putin)的威权统治辩护,指其不比西方国家日益恶化的人权纪录更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如普亭,对异见人士进行了近二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利用一次失败的政变铲除反对党派。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政变夺权后,不断加强镇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公开呼吁将涉嫌吸毒、贩毒者──甚至包括保护他们的人权工作者──就地格杀。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则姑息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对少数教派和族群的恐吓与仇恨犯罪,试图藉此让批评政府的公民组织关门。
在此同时,看穿西方各国偶尔抗议毫不足惧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Bashir al-Assad),靠著俄国、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撑腰,撕毁国际战争法,对该国阿勒颇(Aleppo)东部等反对派占领区的平民加以横暴攻击。数名非洲领导人面对国内或国际控诉自知理亏,竟严词抨击国际刑事法院,其中三人已宣布该国退出该法院。
为制衡上述趋势,亟需广泛重新肯定人权。民粹主义的崛起,势必导致主流政治人物陷入道德挣扎,但不应造成官员或公众放弃根本原则。致力尊重人权的政府比独裁统治更善于防范贪污腐败、自我扩权和恣意妄为,因此能提供民众更好的服务。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政府更能够倾听民意、解民疾苦。尊重人权的政府也更容易在失去人民支持时加以撤换。
但若强人情结和不容忍态度占得上风,世界恐将沦入黑暗时代。我们永远不能低估野心政客,今天他们可以借我们名义牺牲别人的权利,明天当他们真正的目的──保有权力──受阻,就会把我们的权利抛到一边。
特朗普的危险论调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功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是这种不容忍政治的活生生实例。时而明目张胆,时而拐弯抹角,他以违悖尊严与平等基本原则的方式,回应美国人对经济停滞与社会日益多元的不满情绪。他利用刻板形象丑化移民和妖魔化难民,辱骂一名法官的墨西哥血缘,嘲笑一名记者肢体障碍,一再否认性侵指控,并且誓言要让女性自行控制生育的能力向后倒退。
更糟的是,他的论述总是华而不实。例如,他的选战大部分著重于攻击贸易协定和全球经济,但他又把无证移民当做替罪羊,指责他们偷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但他扬言遣返大量移民,包括已在美国安身立命、对美国经济有所贡献者,对找回失去已久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并无助益。美国近年来就业持续增长,而某些人的所得停滞,很难归咎于无证移民,他们的人数近年来没有大幅净增减,而且通常做的是大多数美国公民不愿从事的工作。
候选人特朗普对抗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方案也同样无效──甚至会有反效果──因为他妖魔化穆斯林社群,但穆斯林社群的配合却是侦知恐攻阴谋的关键。他将难民描绘为安全威胁,殊不知他们在入境前受到比一般商务、教育或观光旅客更严格的检验。特朗普不愿限制过度滥用的措施,例如大规模侦监,但这种措施不仅侵犯隐私,而且已证明不比司法监督下锁定对象的侦监更为有效。
特朗普甚至考虑恢复使用某些酷刑,例如水刑板,浑然不知小布什总统的“高级侦讯技术”早已成为恐怖主义召收新血的利器。当他和后来被他提名为国防部长的将军一席谈话后终于知道酷刑没有实效,但这丝毫无法让人宽心,因为他马上又宣称将义无反顾下令实施酷刑,“只要这是美国人民的要求”。谁来诠释美国人民的愿望?大概是他自己。但他忽略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法律和条约都不允许对人施加这样的残酷和痛苦。
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
欧洲也正在兴起一股民粹主义,它将经济停滞归咎于来自欧盟外部或内部的移民。这股潮流最醒目的展现,就属英国脱欧。然而,若支持脱欧人士是为了阻止移民而投下赞成票,代价恐怕是英国经济更加恶化。
在欧陆各国,许多官员和政治人物热中追寻消逝已久、甚至从未存在的纯粹国族主义时代,忽略事实上移民社群在大多数国家早已根深柢固,而来自上层精英的仇外心理不利于促进移民融入社会发挥生产力。某些国家领导人的反难民政策简直是自打嘴巴的悲剧,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即为一例:欧洲过去展臂迎接遭苏联压迫的匈牙利难民,今天欧尔班政府却想尽办法让逃离战火与迫害的新难民度日如年。
没有一个国家有义务接受所有上门求助的人。但国际法对管控移民的手段有所限制。寻求庇护者必须得到公正审判,若其主张合理,应予难民庇护。不得将任何人推回战争、迫害或酷刑。除有特殊例外情况,移民居留多年或与本地人建立家属关系后应给予取得合法地位的途径。不得任意拘押,遣送程序必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各国政府有权禁止和遣返经济移民。
与民粹主义者的诉求不同,政府应充分尊重国内合法居留移民社群的权利。在住房、教育或就业方面都不得有任何歧视。不论法律地位为何,每个人都有权利受到警察保护以及司法系统公正对待。
各国政府应注资协助移民融入并充分参与社会。政府官员特别有责任驳斥民粹主义的仇恨与不容忍论调,表明对法院独立、公正维护人权的信心。这是最好的方式,确保国家在民族日益多元化之后仍能保持民主传统──历史证明,后者是通往繁荣的终南捷径。
特别在欧洲,有些政治人物为了辩护抵制移民──尤其是穆斯林──便指责移民企图复制其所来自的特定国家对女性或同性恋的压迫。然而,回应压迫最好的方法是拒绝压迫──许多移民就是因为受压迫才逃出来的──并且确保社会每一分子都能尊重他人权利。以保护他人权利的名义,剥夺部分社会成员──在当前氛围下主要指穆斯林──的权利,无助于解决问题。权利的选择性适用,将损害权利本质上的普遍性。
土耳其与埃及的威权主义崛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趋独裁专制,足见领导人借口大多数民意践踏人权的危险。近几年来,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改建公园,到修改宪法建立总统制,他对批评其施政计划的人士日渐不予容忍。
过去一年,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发展党利用一场造成数百人牺牲的失败政变发动镇压,对象不仅是他指控策划政变的流亡教士葛兰(Fethullah Gülen)党羽,还包括被认为支持葛兰的其他数千名人士。紧急状态的宣布,成为打压异见人士、关闭独立媒体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大好机会。此外,藉口追查库尔德工人党(PKK),政府将这个亲库尔德族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全都逮捕下狱,该党多名地方首长也遭撤换。
由于许多土耳其民众为政变失败感到庆幸,埃尔多安政府在政变后获得跨党派的广泛支持。但镇压的先例既已树立,司法独立和其他法治规范又受到重创,埃尔多安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扩大打压。西方各国领袖或许还能及时发表强硬的声明,但其他方面的利益,不论是阻止难民涌入欧洲或抵抗自称伊斯兰国的ISIS组织,往往使他们三缄其口。
塞西政府统治下的埃及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由于穆尔西(Mohamed Morsy)总统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短暂执政不得人心,2013年由塞西领导的军事政变获得众多埃及人欢迎。但塞西的高压统治比起长期独裁而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被推翻的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2013年8月,塞西一手主导在一天内杀害至少817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这是当代最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之一。
许多埃及人以为塞西打击的目标仅仅是伊斯兰主义者,但他同时主导扼杀政治空间,关闭所有人权团体、独立媒体和反对党派,拘捕数万囚犯,其中大多遭受酷刑,且几乎不经任何司法程序。
强人的肤浅吸引力
披上大多数民意外衣的民粹主义浪潮,伴随著强人统治的迷思,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倘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重于一切,顺著这种思维,何不乾脆支持那位理直气壮主张“多数决”观点──尽管可能是自私自利──的独裁者,把异议分子踩在脚下。
然而当前这股民粹主义激情很容易让人忽略掉强人统治的长远风险。以普亭为例,俄罗斯的经济就因他所主导的腐败裙带政治而日益衰落,当油价高涨时无法多元发展,一旦油价下跌就面临崩溃。因为害怕2011年起在莫斯科等各大城市爆发的民众示威抗议再起并向外蔓延,普亭企图加以预防,对集会和言论实施严格限制,对网络异议施加前所未有的打压,并瘫痪公民社会组织。
克里姆林宫为了巩固普亭独裁地位,刺激他日渐下滑的支持率,利用俄国占领克里米亚事件在民间煽动民族主义,但却招致欧盟制裁,使下行的经济雪上加霜。他又出兵叙利亚,以俄国轰炸机支持阿萨德对平民的屠杀,导致解除经济制裁从政治角度而言更加遥不可及。直到今天,克里姆林宫的宣传老手们仍试图将经济状况恶化归咎于所谓西方削弱俄国的阴谋。然而,随著经济毫无起色,俄国政府的强词夺理已愈来愈难说服俄国民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走上了类似的镇压之路。中共的高压统治曾经导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由于早期领导人放松经济管制,使中国经济获得傲人增长。然而,政治改革并未跟上经济自由化的脚步,反而随著1989年天安门民运遭镇压而胎死腹中。此后几届政府的经济决策一贯服膺于中共压抑民怨的需求,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高速增长。贪污腐败横行,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大,环境也不断恶化。
同样出于对经济增长趋缓引发民怨的担忧,习近平也开始实施六四以来最激烈的打压行动,使其政府更不受问责。尽管已不厌其烦地给自己加上一长串领导小组的头衔,这位强人的焦虑却似有增无减,因为他仍然无法满足人民对清洁空气、安全食物、公正司法和负责任政府的需求。
同样趋势也出现在其他独裁统治国家。委内瑞拉故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发动、现由其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号称造福贫苦百姓,实则为他们带来经济灾难。民众所得到的是恶性通货膨胀,食物和药品严重短缺,以及在世界石油藏量第一的国家过著穷困生活。政府派出军警临检移民和低收入社区,却四处遭举报侵犯人权,包括法外处决、任意遣返、迫迁和强拆住房。
同时,总统马杜罗操纵司法,派出情治人员任意拘捕、起诉反对党政治人物和民间异见人士,造成占国民大会多数的反对党难以履行立法职能,还通过选举委员会的盟友阻挠罢免公投。
事实上,历来独裁者总是图利自己而非人民。即使是被当做典范的威权主义发展国家,如埃塞俄比亚与卢旺达,其政府制造的祸端也经不起详细检验。埃塞俄比亚政府强迫农民和牧民迁入基本服务阙如的村庄,以便将土地转让给大型农业项目。卢旺达政府以美化市容为名,将小贩和乞丐关进卫生极差的拘留所,还殴打他们。中亚各国在苏联长期统治下民生凋蔽,却盛产政治强人。东南亚各国看似生机蓬勃,如今也因泰国军政府僵化统治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Najib Razak)的政府贪污腐败而使经济发展面临危机。
公民组织与国际刑事法院遭受攻击
非洲人权保障遭遇的最严重威胁,部分源自强人统治者不愿和平转移政权,反而透过暴力和立法压制批评。有些非洲领导人已经废除或延长任期限制──即所谓宪法政变──另外一些领导人则以暴力镇压民众抗议选举不公正或舞弊的活动。赤道几内亚的姆巴索戈(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乌干达的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Robert Mugabe)──在位皆已逾30年──皆已修改宪法继续延任。
近年内各国总统寻求延长任期的行动,有时通过镇压一切反对者而达成,例如卢旺达,有时则通过暴力镇压抗议活动而成功,例如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些国家经常使用类似手段限制公民社会团体和独立媒体,切断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服务,查禁反对党。对公民社会的攻击主要针对资金来源下手──埃塞俄比亚是个中翘楚──这些政府平时积极招引外国援助、贸易和投资,却令人费解地从中作梗,阻挠公民团体寻求海外捐助。
这些政治强人拒绝交出权力,有时是因为在位时曾犯下罪行,担心下台后可能遭到司法追究。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首先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ICC)的计划,因为在他统治期间的暴力镇压已使他成为头号起诉目标。踵继其后的是以独裁统治恶名昭彰的冈比亚总统贾梅(Yahya Jammeh),不过他旋即败选下台,而新任总统当选人巴洛(Adama Barrow)已表示将推翻贾梅退出法院的决定。南非向来是非洲人权与正义的领袖,但总统祖玛(Jacob Zuma)决定启动退出ICC程序,当时他贪污嫌疑缠身,又因公然藐视法院命令、准许遭ICC以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席尔(Omar al-Bashir)逃离南非而遭国内人士质疑违法。在此同时,由于证人受到压力以及政府阻挠检方调查,ICC撤销了对肯尼亚总统肯雅塔(Uhuru Kenyatta)的控诉,导致非洲联盟对ICC的抨击更加猛烈。
不过,少数几名非洲领导人不能代表所有非洲人,由非洲各国公民团体联名支持ICC的行动可见一斑。这些团体并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例如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和加纳。这些非洲人能够看穿所谓ICC是反非洲(anti-African)机构的错误说法。事实上,ICC首席检察官就是非洲人士,她致力于终结有罪免责,因为众多非洲人民都因此惨遭荼毒而求助无门。
ICC在2015全年集中调查非洲受害者,其软肋是美、中、俄等世界强权并未加入。截至2016年11月,该法院尚未对非洲以外初步调查中的数起重大案件正式立案,例如美国官员涉嫌在阿富汗实施酷刑却未被起诉,或以色列官员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建立非法的移民屯垦点。
倘若反对法院的一方真正关注司法公正,他们应当带头鼓励完成前述调查,或施压俄、中两国停止利用安理会否决权阻挠ICC对叙利亚暴行取得管辖权。但他们对更广泛的正义需求不发一言,可见其主要目的是回避解决本国的正义问题。好几个非洲国家希望以一个非洲法院加以取代,让现任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得以豁免控诉,足以说明问题。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攻击不仅来自非洲,但共同目的是企图免除罪责。俄罗斯尚未加入该法院,但当ICC检察官办公室对2008年格鲁吉亚-俄罗斯冲突中可能存在的战争罪行展开调查,以及将乌克兰情势纳入审查之后,俄国便宣布撤回签署──虽然这纯属象征性动作,不具实质意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是在ICC检察官办公室警告杜特尔特鼓吹就地正法可能受到调查后,抨击该法院是个“没有用(useless)”的机构。
ICC的职权是在为内国法院无法处理的世上最严重罪行伸张正义,当然免不了开罪那些不愿被究责的政治强权。它的成效有赖于支持者在政治上和实质上给予坚定奥援。
叙利亚平民遭受攻击
叙利亚或许是当前人权标准面临的最致命威胁。没有比禁止攻击平民更为基本的战时规范。但阿萨德的军事策略一直是恣意且无区别地攻击平民和非军事建筑物,例如医院,只要这些目标是处在该国武装反对团体控制区域之内。
藉著杀伤力强大的空袭攻势,包括“桶爆弹”、集束弹药、密集火炮和偶尔使用的化学武器,阿萨德将叙利亚各大城市里里外外夷为焦土,目的是赶跑所有居民,使反对派武力无法获得根据地。他的策略还包括彻底围困城镇,使居民因粮食断绝而被迫投降。
尽管犯下如此凶残的战争罪行,阿萨德仍自2015年9月起获得俄军支援。他的攻击火力因此大幅提升,策略却未见改变。事实上,他这种战略和克里姆林宫在1999到2000年为歼灭叛军而围攻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手段如出一辙。
这种攻击平民的战争罪行,是造成叙利亚民众大批逃亡的主要原因,国际社会却未尽力法办其罪魁祸首。全国半数人民被迫离乡背井,约480万人已逃往邻近各国,尤其是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其中约有一百万人逃往欧洲。然而西方国家提到叙利亚,总是以ISIS为关注焦点。ISIS的确要为惨无人道的暴行负责,其威胁性也的确远超过叙利亚和伊拉克根据地,但它在叙利亚造成的平民死伤人数远远不及阿萨德。当地信息源估计,叙利亚平民死亡人数约有百分之90应由阿萨德部队及其盟军负责。
由于阿萨德的政治生命现已完全仰赖于俄国军事支援,普亭对阿萨德的行为具有巨大影响力。但我们看不出克里姆林宫曾经善用其影响力阻止平民遭到杀戮。相反地,俄军轰炸机规律性参与攻击行动,悲惨的阿勒颇战役即是一例。
然而,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欧巴马政府,未能下定决心施压俄国善用其影响力,而是著重以俄国为和谈伙伴──即便谈判陷入无止尽的原地打转,而攻击平民的战略造成叙利亚反对派武力日益失去与政府抗衡的筹码。
由其竞选言论来看,总统当选人特朗普似乎决心让美国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ISIS,甚至提议为此与普亭和阿萨德站上同一阵线,显然忽略他们对付ISIS多么漫不经心,而且他们的暴行正好有助于ISIS不断补充新血。即便ISIS最终遭到军事挫败,那些暴行也很容易催化出新的极端组织,正如ISIS本身也是因为同样的暴行而由伊拉克盖达组织的馀烬中窜起。
重新肯定人权价值的必要
为了抵抗当前对人权的全球性攻讦,必须强烈地重申和捍卫做为人权基础的一些基本价值。
许多人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公民社会团体,特别是维权组织,必须保护面临威胁的公民行动空间,建立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盟以彰显共同的人权关注,拉近南-北分歧以团结力量对抗显然正在互相学习的各国独裁者。
媒体机构应协助凸显这种危险趋势的临近,在报导当天人物言行的同时,分析其长期后果,尤应加强揭露和驳斥特定党派人士的政治宣传及其炮制的“假新闻”。
自诩尊重人权的各国政府必须拿出更加一贯的态度,为基本原则辩护。这包括拉美、非洲和亚洲的民主国家,它们虽然经常投票支持其他国家倡导的议案,但不论在联合国或在各自的双边外交上都很少发挥领导作用。
最终,责任在于大众。野心政客不断散播似是而非的观念,对真正的问题提出错误的解释和廉价的解决方案,藉此累聚民众支持。拨乱反正的最佳途径,就是由大众要求将政治建立在尊重人权的民主政治所以依存的真理与价值之上。若不存在反对的声音,民粹主义者将大行其道。唯有民间强劲反击,发动一切可用工具──公民组织、政治党派、传统与社交媒体──才能保卫那些即使在患难中仍为许多人所珍视的价值。
谎言不会因为大群网军或党徒反覆宣传就变成真理。以讹传讹的回声效应并非无往不利。正因事实毕竟胜于雄辩,独裁者才极力检查言论,打压对其不利的真相、尤其是人权侵害的报导。
价值是脆弱的。由于人权价值首先取决于同情他人的能力──肯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重要──很容易因为野心政客的排他诉求而动摇。一个社会必须不断滋养尊重人权的文化,才不会因为一时的恐惧而放弃民主政治所以奠基的智慧。